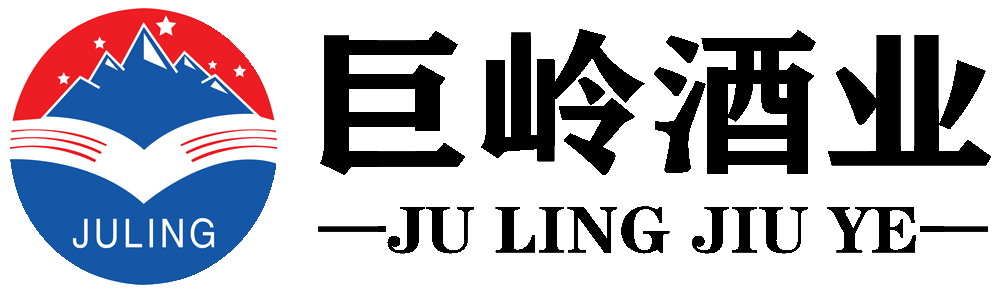首頁 > 政經要聞 > 詳情 政經要聞
人民幣貶值1.4%引發的震蕩與思考
【財新網】(專欄作家 梁紅)
開年兩周,人民幣匯率超預期震蕩,但調整效果有限,累計貶值僅1.4%。前四天,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較前日收盤價連續走弱,而美元指數并未明顯走強,因此被市場解讀為央行有意貶值。在岸和離岸即期匯率相應下挫,引發市場恐慌,兩地匯差創歷史記錄。隨后,人民幣在岸中間價和即期匯率回調,離岸匯率被迅速拉升,匯差收窄、甚至短暫倒掛。離岸人民幣隔夜拆借利率創下歷史新高,于12日飆升至66.8%。雖然市場暫穩,但貶值壓力并未得到充分釋放,跨境套利空間依然存在。
人民幣不多的貶值卻引發了國內外資本市場的連鎖反應。元旦以來,上證綜指累計下跌18.3%,滬深300四次熔斷、深跌16.4%。美股出現四年多來最大雙周跌幅,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分別下跌8.1%和10.4%,德國DAX指數跌11.2%,恒生指數跌10.9%,韓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均表現不佳。大宗商品價格同樣大幅下挫,布油下跌22.6%,跌破30美元/桶,銅、鐵礦石、鋁、鋅等也均處于跌勢。更令人意外的是,港幣出現急貶,14和15兩日跌幅為1992年來最高。全球唯有避險資產獲青睞,10年美債收益率一度跌破2%,中債跌至2.7%附近,黃金上漲2.6%。人民幣匯率的不確定性不是引發國際市場動蕩的唯一原因,但它在已然脆弱的市場情緒下,進一步壓制了風險偏好,無疑是重要的催化劑。
匯率政策的不當操作會加劇貶值預期,可能引起外匯儲備降幅擴大,甚至可能造成一些改革措施倒退。去年8月11日中間價改革引發人民幣貶值預期,但在央行干預后,貶值預期有所消散,維穩成本下降,其中10月份外匯儲備還增加了114億美元。然而,在12月初發布CFETS人民幣指數、尤其新年又放手急貶后,政策意圖令人困惑。原已消退的貶值預期卷土重來,而且來勢更猛。尤其,個人原非外匯市場主要參與主體,但也受預期影響集中增持外匯,加深了恐慌情緒。或是對市場反應估計不足,央行在貶值后重拾干預措施,并將之擴展至離岸。措施反復不僅抵消了前期調整效果,而且可能放大1月份外儲降幅。原已市場化的中間價又陷入無彈性狀態,被市場解讀為央行操控的結果。相關部門引入了新的管控措施,暫停了一些資本開放項目。即便這些措施是暫時的,但其對政策信譽的損害或已形成。
往前看,市場的劇烈震蕩和風險上升應引起決策者對匯率政策選擇的再思考。在目前情形下,無非三種選擇:
► 保持匯率穩定(“利人利己”)。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大貿易體,通過貶值刺激出口的空間有限。經此番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和一籃子貨幣實際貶幅都不大。對中國,在外匯市場不成熟的情況下,“匯率彈性”已成為新的不確定性的重要來源,而非抵御外部沖擊的緩沖機制。對世界,在經濟不穩、情緒脆弱的環境下,人民幣波動抬高風險溢價,對全球、尤其新興市場構成沖擊,引發連鎖反應,最終也會影響到中國自身。相反,若央行保持匯率穩定并一以貫之,那么貶值預期在一段時間后會自然消退,匯率穩定下來,干預成本亦會相應下降。隨著經濟形勢好轉、人民幣支撐增強,匯率彈性擴大會迎來更好的契機。
► 一次性貶值(“損人可能利己”)。一次性貶到位可能會給國內外市場帶來較大沖擊,但有助于充分釋放市場壓力,使人民幣在新匯率水平上企穩。當然,貶值空間不是無限的。根據我們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或跌至6.87元/美元,即便超調,超出幅度也不會太大。
► 漸進式貶值(“損人也不利己”)。在漸進式貶值路徑上,貶值預期自我實現,資本加速流出,政府不得不配合以資本管制措施,資金和制度成本巨大。與此同時,全球風險偏好受抑制,投資、消費等經濟活動放緩,最終拖累世界和中國經濟增長。最近對港幣匯率制度的沖擊在一定程度上也與人民幣政策的這一傾向有關。
從成本收益分析,加強匯率穩定應是目前最佳的政策選擇。在短期經歷了兩三輪調整后,市場對政策一致性或有不信任,貶值預期應比上一輪更難被打消,維穩成本升高。在此情形下,合理選擇、加強溝通并果斷執行顯得尤為重要。若操作不當,根據新興市場國家經驗,隨著外儲下降、市場信心動搖,最終被迫貶值,其貶幅和影響往往超出決策者當初的想象。穩增長才是當務之急,匯率政策不應成為新的主要風險因素。
最后,這些風波也會提醒決策者對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及其中離岸市場的角色進行反思。離岸市場為人民幣走向國際舞臺提供了通道,這在國內金融市場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非常重要。從某種程度上講,離岸市場誕生于監管套利,必然會對國內宏觀政策構成挑戰。隨著市場規模擴大,這種挑戰越來越不容小覷。央行在離岸市場較大動靜的干預措施,使離岸人民幣流動性一度告竭。此舉可抑制針對人民幣的投機行為,但也會抵消之前為培育離岸市場發展所做的努力,使離岸人民幣的可投資性受損。對兩地匯差和套利行為,是疏還是堵?如何平衡離岸市場發展的利弊?這些問題尚有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