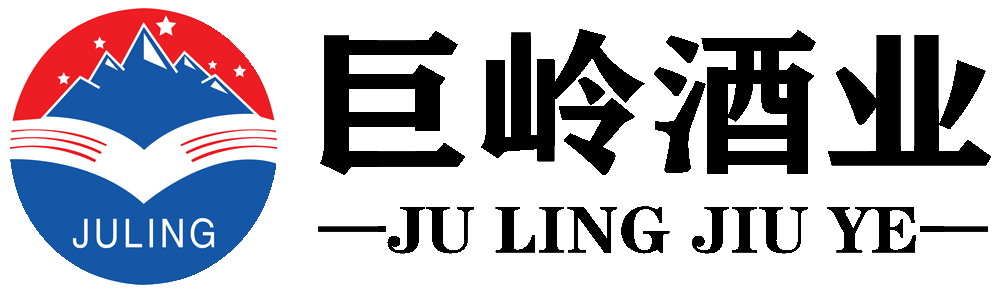首頁 > 政經要聞 > 詳情 政經要聞
2021年金融系統防風險:防不良和杜絕灰犀牛是主組件
發布日期:2021-3-24 11:31:34 瀏覽次數:1212次 【關閉窗口】
銀行業2020年共處置不良資產3.02萬億元,為歷年最高;新提取撥備1.9萬億元,同比多提取1139億元。
2020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收官之年,而防風險亦是2021年金融監管主題之一。
在去年國企債券違約、部分中小金融機構被接管等事件發生之后,業內人士表示,2021年仍需警惕“灰犀牛”風險,特別是對于杠桿率較高的企業尤為關注。此外,隨著延期還本付息政策退出,銀行資產質量仍面臨一定壓力。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上表示,今年中國經濟應該可以實現、甚至超過8.1%的增長速度,但確實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包括疫情風險、自我增長能力弱和金融風險等因素,值得高度關注。
不良壓力有多大?
若從中觀數據看,受商業銀行加大力度處置不良影響,2020年不良壓力并未大幅上升。根據銀保監會數據,截至2020年末,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3.5萬億元,較年初增加2816億元;不良貸款率1.92%,較年初下降0.06個百分點。其中,國有行不良率1.52%,較三季末提升0.02個百分點;股份行、城商行和農商行不良率分別為1.50%、1.81%和3.88%,較三季末分別降低0.13、0.47和0.29個百分點。
究其原因,銀行業2020年共處置不良資產3.02萬億元,為歷年最高;新提取撥備1.9萬億元,同比多提取1139億元。對于2021年不良資產,“可能2021年需要處置的不良貸款還會增長,甚至會延續到明年,因為有的貸款期限比較長。”3月2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但是,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把不良資產處置處理好。第一要加大力度,第二要穩中求進,保證在經濟和銀行金融體系的可承受范圍內。”郭樹清表示,疫情發生以后,一些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肯定處于不正常的狀態,還款就會有困難,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可能會面臨破產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狀況,更沒有能力償還貸款。所以不良貸款上升是必然趨勢。
不良貸款壓力之一來自延期還本付息政策退出。根據央行等五部門此前發布的通知,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政策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谷澍指出,去年延本延息部分貸款節點是3月31日。該行這段時間一直都在監控這部分貸款的資產質量情況,從目前的情況看,比普通貸款不良率高一些,但是仍然可控。從農行的樣本來看,受疫情影響,不良貸款的反彈風險是有的,但是風險是基本可控的。為處置不良,今年1月,銀保監會下發通知,批準銀登中心開展單戶對公不良貸款轉讓和個人不良貸款批量轉讓試點,進一步拓寬不良貸款處置渠道和處置方式。3月1日,首批共6個參與個人不良貸款批量轉讓和單戶對公不良貸款轉讓試點的資產包陸續進入競價環節。其中,3個個貸不良資產包和2個單戶對公不良資產包來自工商銀行,1個個貸不良資產包來自平安銀行。
防范“灰犀牛”風險
“今年我們最警惕的是灰犀牛風險,不良可以多處置,但灰犀牛很難防范。”今年3月,一位沿海城商行總行人士表示,大中型企業單體規模太大,一旦發生不良數量陡升,銀行想抽身也很難。從監管角度,“灰犀牛”風險在于房地產。郭樹清表示,房地產的問題是金融化、泡沫化傾向還比較強,但是去年投向房地產的貸款增速第一次降到了平均貸款增速之下,這個成績來之不易。“我們相信,房地產的問題會逐步得到好轉。”
他指出,說到“灰犀牛”問題,很多人買房子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投資或者投機,這是很危險的。因為持有那么多房產,將來這個市場要是下來的話,個人財產就會有很大的損失,貸款還不上,銀行也收不回貸款本金和利息,經濟生活就發生很大的混亂。所以必須既積極又穩妥地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對于金融機構,上市公司、國企等原被認為安全邊際較高的公司,亦是違約風險來源之一。如,對于剛發生違約的華夏幸福,平安集團董事總經理兼聯席CEO謝永林在2020年度業績發布會上說,華夏幸福僅是中國平安8萬億組合投資的一小部分,風險敞口約540億,其中股權投資180億,表內債券投資360億。華夏幸福近兩年出現流動性困難和債務危機,主要受三方面影響:一是環京津冀的嚴格調控直接影響了華夏幸福的回款;二是疫情影響;三是管理層的管理模式粗放且擴張太快,導致華夏幸福經營遇到比較大的困境。
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數據,2020年我國宏觀杠桿率270.1%,環比上行23個百分點,是2009年以來最高漲幅。分部門看,企業部門加杠桿幅度最大,其中居民部門、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分別上行6.1、7.1、10.4個點。
保持金融機構穩健性
防風險的關鍵,在于金融機構運行的穩健性。黃益平指出,去年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力的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但有些后遺癥可能會在今年暴露。發放這么多中小微企業貸款,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會出現風險。所以今年債券市場(尤其是信用債)違約率和商業銀行的不良率都可能會上升。他表示,這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兩方面影響。一是隨著資產質量下降,金融機構自身的穩健性是否會出現問題、風險會提高到什么程度,會不會形成系統性的風險。二是未來金融機構是否有足夠的資本金和流動性來支持實體經濟的增長,這不僅關乎怎樣化解去年的風險,還影響到今年增長的持續性。
監管機構也注意到這一風險,陸續對金融監管開展壓力測試。對于保險公司,3月1日,多家媒體報道,近日銀保監會下發通知,要求在去年第四季度償付能力數據的基礎上,測算六類壓力情景下的償付能力相關指標變化。包括:權益類資產下跌情景、交易對手違約情景、利率下降情景、重疾發生率惡化情景、退保率變化情景、賠付率惡化情景。
去年11月,央行發布金融穩定報告稱,2019年上半年央行選取1171家銀行開展壓力測試,測試內容包括償付能力壓力測試和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評估銀行體系在“極端但可能”沖擊下的穩健性狀況。結果顯示,30家參試銀行整體抗沖擊能力較強,而信用風險是主要風險來源。
此外,2月26日晚,銀保監會公告,對《銀行保險機構恢復和處置計劃實施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金融機構的恢復與處置計劃,也被稱作“生前遺囑”,哪些銀行會被納入需制定“生前遺囑”的范圍,根據“調整后的表內外資產余額”口徑,大部分上市銀行即已達到3000億元標準,包括六大國有銀行、12家股份制銀行、11家上市城商行,但農商行大多不及這一標準。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應對氣候變化金融風險面臨較大挑戰。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月25日,央行研究局局長王信最新撰文稱,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被認為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之一,中國在該領域的風險評估和應對上亦面臨較大挑戰;未來應強化氣候風險應對的頂層設計和宏觀審慎管理,如及早開展氣候變化對金融體系影響的情景分析與壓力測試。他表示,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應要求金融機構合理測算高碳資產風險敞口,將環境風險納入其風險管理框架,定期開展環境風險評估和壓力測試;金融機構應及時披露資產組合的碳排放量和強度等。
2020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收官之年,而防風險亦是2021年金融監管主題之一。
在去年國企債券違約、部分中小金融機構被接管等事件發生之后,業內人士表示,2021年仍需警惕“灰犀牛”風險,特別是對于杠桿率較高的企業尤為關注。此外,隨著延期還本付息政策退出,銀行資產質量仍面臨一定壓力。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上表示,今年中國經濟應該可以實現、甚至超過8.1%的增長速度,但確實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包括疫情風險、自我增長能力弱和金融風險等因素,值得高度關注。
不良壓力有多大?
若從中觀數據看,受商業銀行加大力度處置不良影響,2020年不良壓力并未大幅上升。根據銀保監會數據,截至2020年末,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3.5萬億元,較年初增加2816億元;不良貸款率1.92%,較年初下降0.06個百分點。其中,國有行不良率1.52%,較三季末提升0.02個百分點;股份行、城商行和農商行不良率分別為1.50%、1.81%和3.88%,較三季末分別降低0.13、0.47和0.29個百分點。
究其原因,銀行業2020年共處置不良資產3.02萬億元,為歷年最高;新提取撥備1.9萬億元,同比多提取1139億元。對于2021年不良資產,“可能2021年需要處置的不良貸款還會增長,甚至會延續到明年,因為有的貸款期限比較長。”3月2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但是,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把不良資產處置處理好。第一要加大力度,第二要穩中求進,保證在經濟和銀行金融體系的可承受范圍內。”郭樹清表示,疫情發生以后,一些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肯定處于不正常的狀態,還款就會有困難,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可能會面臨破產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狀況,更沒有能力償還貸款。所以不良貸款上升是必然趨勢。
不良貸款壓力之一來自延期還本付息政策退出。根據央行等五部門此前發布的通知,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政策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谷澍指出,去年延本延息部分貸款節點是3月31日。該行這段時間一直都在監控這部分貸款的資產質量情況,從目前的情況看,比普通貸款不良率高一些,但是仍然可控。從農行的樣本來看,受疫情影響,不良貸款的反彈風險是有的,但是風險是基本可控的。為處置不良,今年1月,銀保監會下發通知,批準銀登中心開展單戶對公不良貸款轉讓和個人不良貸款批量轉讓試點,進一步拓寬不良貸款處置渠道和處置方式。3月1日,首批共6個參與個人不良貸款批量轉讓和單戶對公不良貸款轉讓試點的資產包陸續進入競價環節。其中,3個個貸不良資產包和2個單戶對公不良資產包來自工商銀行,1個個貸不良資產包來自平安銀行。
防范“灰犀牛”風險
“今年我們最警惕的是灰犀牛風險,不良可以多處置,但灰犀牛很難防范。”今年3月,一位沿海城商行總行人士表示,大中型企業單體規模太大,一旦發生不良數量陡升,銀行想抽身也很難。從監管角度,“灰犀牛”風險在于房地產。郭樹清表示,房地產的問題是金融化、泡沫化傾向還比較強,但是去年投向房地產的貸款增速第一次降到了平均貸款增速之下,這個成績來之不易。“我們相信,房地產的問題會逐步得到好轉。”
他指出,說到“灰犀牛”問題,很多人買房子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投資或者投機,這是很危險的。因為持有那么多房產,將來這個市場要是下來的話,個人財產就會有很大的損失,貸款還不上,銀行也收不回貸款本金和利息,經濟生活就發生很大的混亂。所以必須既積極又穩妥地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對于金融機構,上市公司、國企等原被認為安全邊際較高的公司,亦是違約風險來源之一。如,對于剛發生違約的華夏幸福,平安集團董事總經理兼聯席CEO謝永林在2020年度業績發布會上說,華夏幸福僅是中國平安8萬億組合投資的一小部分,風險敞口約540億,其中股權投資180億,表內債券投資360億。華夏幸福近兩年出現流動性困難和債務危機,主要受三方面影響:一是環京津冀的嚴格調控直接影響了華夏幸福的回款;二是疫情影響;三是管理層的管理模式粗放且擴張太快,導致華夏幸福經營遇到比較大的困境。
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數據,2020年我國宏觀杠桿率270.1%,環比上行23個百分點,是2009年以來最高漲幅。分部門看,企業部門加杠桿幅度最大,其中居民部門、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分別上行6.1、7.1、10.4個點。
保持金融機構穩健性
防風險的關鍵,在于金融機構運行的穩健性。黃益平指出,去年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力的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但有些后遺癥可能會在今年暴露。發放這么多中小微企業貸款,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會出現風險。所以今年債券市場(尤其是信用債)違約率和商業銀行的不良率都可能會上升。他表示,這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兩方面影響。一是隨著資產質量下降,金融機構自身的穩健性是否會出現問題、風險會提高到什么程度,會不會形成系統性的風險。二是未來金融機構是否有足夠的資本金和流動性來支持實體經濟的增長,這不僅關乎怎樣化解去年的風險,還影響到今年增長的持續性。
監管機構也注意到這一風險,陸續對金融監管開展壓力測試。對于保險公司,3月1日,多家媒體報道,近日銀保監會下發通知,要求在去年第四季度償付能力數據的基礎上,測算六類壓力情景下的償付能力相關指標變化。包括:權益類資產下跌情景、交易對手違約情景、利率下降情景、重疾發生率惡化情景、退保率變化情景、賠付率惡化情景。
去年11月,央行發布金融穩定報告稱,2019年上半年央行選取1171家銀行開展壓力測試,測試內容包括償付能力壓力測試和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評估銀行體系在“極端但可能”沖擊下的穩健性狀況。結果顯示,30家參試銀行整體抗沖擊能力較強,而信用風險是主要風險來源。
此外,2月26日晚,銀保監會公告,對《銀行保險機構恢復和處置計劃實施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金融機構的恢復與處置計劃,也被稱作“生前遺囑”,哪些銀行會被納入需制定“生前遺囑”的范圍,根據“調整后的表內外資產余額”口徑,大部分上市銀行即已達到3000億元標準,包括六大國有銀行、12家股份制銀行、11家上市城商行,但農商行大多不及這一標準。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應對氣候變化金融風險面臨較大挑戰。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月25日,央行研究局局長王信最新撰文稱,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被認為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之一,中國在該領域的風險評估和應對上亦面臨較大挑戰;未來應強化氣候風險應對的頂層設計和宏觀審慎管理,如及早開展氣候變化對金融體系影響的情景分析與壓力測試。他表示,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應要求金融機構合理測算高碳資產風險敞口,將環境風險納入其風險管理框架,定期開展環境風險評估和壓力測試;金融機構應及時披露資產組合的碳排放量和強度等。